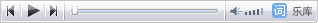十年前,我毛竹从鲁院高研班结业后,到青海探亲。抽空儿,我去看青海作家陈元魁夫妻。陈元魁是我写作起步的启蒙师。
陈元魁的第三部大著《花儿怨》已经出笼,正在寻找婆家。
这之前,偶从青海的朋友的手中看到青海各杂志上连载的陈元魁的书《花儿怨》,喜欢,想多看,就给陈元魁打电话。陈老师居然给我寄来了一大堆杂志。这让我再一次感觉到了陈元魁对我的看重。因为这种杂志,一般作者手中只有一两本样刊,不可能多,可是陈元魁老师却把他手中的需要珍藏的一两本都寄给了在北京的我。上一次《麒麟河》出书前,也是如此。
我到了陈元魁老师家。那时陈元魁老师还住在青海日报的院子里。陈元魁老师的客厅挂着《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诠释作者甄士隐。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我再一次感觉我给陈元魁老师的定位是多么的准。我曾写陈元魁的文章《贾宝玉在青海投身转世》
我看了陈元魁的手稿,再一次感觉写得好,再一次感觉写得有氛量。
陈元魁给我谈了这本书的将出版情况。大约是有爱才人士帮助从上面要了三万元资助,出版社表态除了这三万元,可先不要书号费与印刷费,待书出版后,再从回款中扣除。当然预计该书在青海发行形势大好,可是全国发行仍是问题,因为,陈元魁写的书是青海人民熟悉的生活。稿费大约需要陈元魁自己发行一部分书。也就是出版社拿书当稿费。
我觉得这种出版,会再一次把一本好书囿在青海。我认为这样出版,对不起写得这么好的《花儿怨》。
我就建议由我把书稿带到北京替他寻找出版社。虽然,几年前,陈元魁的《麒麟河》在青海各杂志连载轰动无比,书稿陈元魁交给我,由我带到北京作家出版社副社长。副社长好像很重视,与陈元魁沟通数次,但是最终出版并无下文。书稿最后被副社长退回了青海。这一次我愿意再为陈元魁去碰一次钉子。为了劝说陈元魁同意我的举动,我告诉他,今非昔比!我毛竹刚从鲁院高研班毕业,中国十大名编都是我的导师,都期待我们交上或推荐好书稿。我特别地提到我的导师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潘凯雄。
我回到了北京,陈元魁给我打来电话,经过考虑,他把他的书稿《花儿怨》从青海人民出版要了回来,全权交给了我。
我全面考虑了一下,就把书稿唯一地用电脑点给了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位置调离的潘凯雄。潘凯雄调到了中国出版集团任副总裁。虽然官升高了,但是我估计做出版事儿却没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带劲儿。潘恺雄一定不奇怪,毛竹对他的直升表示同情。
我怕潘凯雄老师忙没有时间看,我接着给潘凯雄老师发信息 。
"请潘导师百忙中一定一定挤时间看一下陈元魁的《花儿怨》。全中国出版界的出版家毛竹只发给您一个人。且此书稿我不会再发给第二个人。请相信,一般的作品毛竹绝不会推荐给您。请相信,只要您看完它,您就会相信毛竹的眼力还不错。"
然后这事儿我就放下了。我期待着潘凯雄百忙中真的能看。但也只能是期待。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偶尔给潘导师发一个问候信息,暗示一下,再忙也不要忘了读我推荐的书,我们都等着呢。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
第二年,我去上海过春节,有一天我接到了潘凯雄亲自打来的电话。潘凯雄十分兴奋,说了许多的话,感谢我给他推荐了这么好的书稿。我放下电话,就给陈元魁打过去电话,汇报了潘凯雄的评价,显然我们三个都很兴奋。虽然兴奋点不同。
然后书稿被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赵萍编辑。赵萍是毕飞宇《推拿》的责编。《推拿》获得第八届茅奖,被改编成电影在中国影响大大的。赵萍拿到书稿《花儿怨》后也很兴奋,想压着点儿出版。也就是赵萍要控制好其出书的时段,目的是可拿《花儿怨》去冲击第九届茅奖。赵萍希望她编辑的书能再一次荣获茅奖。
这一压就是近半年。期间陈元魁夫妻来京下塌我所在的中国石油报宾馆。这也是青海阿门了陈元魁第一次来京。那一次我家正在忙装修房子,我仅陪陈元魁夫妻去了一趟后海。
陈元魁老师告诉我:为了把书稿《花儿怨》从青海人民出版社拿出来,他还陪进去三千元的违约金。可是这边迟迟没有下文,我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别把陈老师闪了。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
我想起一青海文友给我说,陈元魁曾到他办公室推销书60万字的《民生街》,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拿自己的钱买下一百套,还撒谎说办公室给公司要的。青海文友对我说:陈元魁给我说,他还要再写第三部。青海文友感叹道:你说这个陈元魁,到底是图个啥吗?
可不是?中国真正的酸文人,整天看似忙忙碌碌,但是都是一场空,到底是为了了啥吗?生命苦短,命运苦多,这般痴心不改,痴心不移,可是大滚滚红尘中,真正的酸文人轻如鸿毛,惺惺相惜。孤独无助,四面楚歌,绝地自战。 、
到底图个啥吗?这声音在我的生命反复轰响,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
如果普通的作家出书这样自己推销没什么,可是青海像昌耀、陈元魁、我爸爸大巴山人毛高畴类灵魂有超级吨位的作家亲自去推销自己的书,我的心里不能不风雷撼动。
陈元魁在父亲做为一个旧时代文员,在新时代找不到工作,60年是被饿死的,孤坟一个是埋在陌生农村乡下的--正是因为陈元魁的叙述让我注意到了中国那一批孤坟埋在农村乡下的人,包括我的爷爷毛远稚与两个徐姑婆与河口徐大公子,他们都是旧时代的管家与管家婆。不几年陈元魁的母亲也随风而去。陈元魁做为陈家唯一的儿子,多年后回忆这两件事儿,认为父母的死与自己的无力照顾甚至不会照顾相关,这才开始自责。这也是陈元魁写的另一个原动力。陈元魁成了孤儿,是姐姐供他。生活越来越难,姐姐、姐夫供不下去了,陈元魁无奈只好去当兵。在姐姐、姐夫的帮助下,陈元魁在姐夫家的地里盖了一间干打垒,居然娶上了一个媳妇。因为与媳妇没有感情基础,陈元魁与厂里一位有点财权的女人相爱。结局是第一位媳妇病逝后,给他留下三个幼女。那位女人犯事儿。陈元魁落了一个两手空空,只剩对三个女儿的扶养责任。陈元魁接着找了一位下放农村城里人家的大龄姑娘---岳父下放后,对农村人非常不满,表态女儿非城里人不嫁,哪怕二婚,让姑娘成了大龄“剩女”。这么多年,陈元魁的农村妻子进城当后妈是没有工作更没工资的。我是看着陈元魁的三个女儿慢慢长大的。陈元魁那会儿全家五口,就靠陈元魁一个人的工资生活。陈元魁从部队下来在青海某厂工作一段,由于喜欢写作,在外省发表了作品,被青海日报王文泸与邢秀玲欣赏,调入青海日报社文艺部。因为没有正规学历,没有正规级别,陈元魁的工资从来都不高。陈元魁经常捉襟见肘。陈元魁经常在走投无路时,才开口向朋友们借钱。好不容易开口,却常碰钉子,这让陈元魁变得更加多愁善感。后来陈元魁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了,陈元魁又像玩“过山车“一般玩起了惊险的房产运作。陈元魁卖房、买房、借钱、按揭。从青海日报家属院搬出,换了一个能见南山的、有书房的房子。我知道这贷款的钱最后惊险还上。这让陈元魁全家均魂动魄动。这其中一部分钱,甚至包括了吉狄马加在青海当副省长时,准备拍陈元魁的《麒麟河》为电视连续剧,提前给作者陈元魁预支的20万订金。马加副省长调回北京后,《麒麟河》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拍摄工作不了了之。可是如果电视台要求退订金呢?陈元魁的惊险运作,让所有知内情的朋友都替他揪心。还好,总算有惊元险,电视台没有提退订金之事儿。一个小小的弱弱的孤独的无助的执着的作家,终于住上了能见南山能有书房的房子。
直到两大套上下集一百二十万字著名在青海省轰动以后,陈元魁写后记,这个大作家居然以满足于早上能喝上牛奶吃上馍馍,没有饿肚子而满足,而幸福。原来陈元魁是近代饿死酸文人的后裔呀!
其实,我比陈元魁本人更希望《花儿怨》顺利出书。我毛竹的这份儿小小的愿望,居然是青海以外唯一个中国文人的小小祈祷。是呀,茫茫大千世界,中国十四亿人,除了青海600万中有一两万人关心陈元魁创作的,其它35个省世自治区,关心陈元魁创作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小小的毛竹。
那时候,全中国都没有人知道,有空儿,小小毛竹就在心里默默祈祷,愿好运伴随《花儿怨》顺利出版。
那一段时间,我常想起这样一句青海花儿:麦杆儿搭了一个闪闪的桥,你说是牢还是不牢?
那一段时间,我常常自责,你看人家陈元魁的书在青海出版好好的,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你非要没事找事把陈元魁的书拿到北京交给潘凯雄、赵萍出版,万一这中间遇到什么坎儿,叫你毛竹如何面对对你如亲人一般的陈元魁一家人!更重要的是,若再次推荐失败,让毛竹情何以堪。
恍惚是等了几个世纪,《花儿是心上的油》终于出版了。赵萍把书名改了《花儿是心上的油》。陈元魁与我都觉得书名叫《花儿怨》更好,因为陈元魁近200万字的巨著《麒麟河》《民生街》《花儿怨》是三部曲呢。而我认为叫《花儿囿》书名更好。花儿在青海祁连山村庄中属于禁歌,在家在村里在老人面前是不能唱的。花儿囿,是青海祁连山老百姓生命中灵魂如帝王贵族一般进行狩猎、游乐的园林形式,因为花是禁歌,通常选定地域后划出范围,或筑界垣,或在深山大野中才能野唱。花儿囿中生命中的草木鸟兽自然滋生繁育。花儿是农民生命中“神秘灵魂囿园”,花儿是农民灵魂中的”秘密‘皇家’囿园”。而青海农村的庄廓正是囿状的,庄廓中的秘密,不是正是此书的主题,花儿是农民心中的秘密?花儿囿,又是青海东部农业区的山民们在生命中养动物的园子,因为那是原始欲望冲动的地方。 囿又表达被局限,被限制:生命的欲望囿于身体中,成为秘密。 花儿囿,可借指现实生活之外,山民的精神世界。囿形状如同书中女主角的眼睛,那美丽眼睛中的秘密,那多情眼睛中的玄机,那深邃眼睛中的机密,不正是囿中的秘密?不正是《花儿怨》主题。囿是一个有张力有内涵有寓意的字儿。而囿与怨比,显然囿更耐人寻味儿,更像小说标题中的关键字儿。而一个“囿”字可以把书的档次提高好几个层次。如果第九届茅奖送作品时,送的不是《花儿是心上的油》而是《花儿囿》,说不定《花儿囿》已经获茅奖了。(真心话大冒险,毛竹心里冒出的这个书名《花儿囿》真是太精彩了,时间会告诉文友们,毛竹这个新书名的蕴含。特别是你们有空儿看了陈元魁的书,才会明白《花儿囿》这个书名字起绝了,方可明白《花儿囿》是一个获得茅奖的书名呀!真可惜出版前赵萍编辑没有与推荐者毛竹沟通一下。《花儿囿》这个点睛且耐人反复思考回味的书名,足可以把陈元魁的书,从第九届茅奖第三十七名,抬高到前十名以内。写到这里毛竹笑了,你们笑了吗?但这话的确是从心里冒出来的,你们就笑纳吧!陈元魁也同意我的分析,准备再版时改书名。但是《花儿是心上的油》再版遥遥无期这是一。再版改书名又是不容许的,除非重新排版出修订版。我只笑一笑,留下这个好书名。
青海方出版社在大力配合?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陈元魁的另一本书《一生能做几件事》。其中出现毛竹照片,下面署名,居然不是”我的学生毛竹“,而是”我文友毛竹“。我心里有风雨感动。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初相识,陈元魁对我就是全方位地欣赏。他的出现不是来教导我的,而是与我分享写作快乐的。而是拿出他的草稿,希望我来评价,给他鼓励的。我们俩个人,一个灵感多多,一个是技巧过硬。我们在一起探讨多的也是这个。我这个灵感风起云涌的人需要的正是技巧。而他这个技巧过硬的人,需要的正是我那风起云涌的灵感。我知道,我们两个有在青海认识到我进京,有几年时间,经常来往,探讨写作与艺术。而我们在一起谈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争吵。现在想起,我那时怎么有那以多的话?正可谓如大江滔滔,如大海奔涌。我的观点太多,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一般的男人遇到一个女人这么有思想有论点有见解有内在泉涌有突破见解,可能早就吓跑了,可是陈元魁老师不同。我们棋逢对手。我们的”思想大军“可展开全面激战,而互不让一分。那是真正的精神大战,常常风雷激荡,海潮海啸。还有一点,我再怎么暴风骤雨,他都平静如一而镜子,适合我照。我再怎么激情万丈,我不会丢失他。这也是当年在青海,那么多的关注新秀毛竹的人,可是毛竹却唯独与其貌不扬的小个子陈元魁走得最近的原因之一?
当然与他走得近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我漂亮吗?我美丽吗?我优秀吗?我出色吗?我不知道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可能许多人觉得年轻的我美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可是没有一个人肯说出来,没有一个人肯全方位的赞美我,让我可是在受伤后需要在这赞美才我粘合破碎的自己。但是,我只在寻找一种再生的粘合力,我只希望粘合好自己让我在乎的情人远看,让我在乎的离人后悔,让我丢失的一切重新回来。我知道我对陈元魁绝对不是被众人误解的那种感情。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没有这份友谊。没有这个大朋友,我担心刚粘合的自己会再次碎了,消失无踪迹了。所以在我生命的某个时段,我就会机械地跑到青海日报办公室或是陈老师家去看陈元魁。
有一次我回西宁,当时在西宁晚报的赵秋玲请我吃饭,知道我与陈元魁关系好,就把陈元魁也叫上了。吃完饭,我们走在北门坡上,赵秋玲说:”我先走了,你们两个好不容易见一面,我就不在中间当灯泡了!“我们两个人看赵秋玲走了,然后对视就开始笑,笑得肚子都痛了。陈元魁说:我们俩个是不是应当再好些,像文友们猜的那样,这样才能不负众望。我毛竹说:是呀!你看我们这样,不好又挺好,挺好又不好,道是无情似有情。是不是辜负了文友们,这些辜负的文友现在不仅包括以赵秋玲、肖黛为代表的西宁朋友,以梅洁为代表的河北文友们,还有以文化部长某某为代表的北京文友们,还有我的以冯敬兰为代表的石油文友们............还有以周篷桦为代表的我的鲁院高研班的校友们。
《花儿是心上的油》冲击第九届茅奖获前三十七名的好成绩。这对一位在全国名不见经传的青海作家陈元魁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虽然赵萍略有失望。(毛竹调侃:这次失败正是因为没有用毛竹提议的好书名《花儿囿》引起的。如果书名是耐人寻味的《花儿囿》而非《花儿是心上的油》,陈元魁得茅奖希望大大的。也就是赵萍出书前因当与推荐人毛竹好好沟通一下)。
您想想,北京作家王蒙,五十年代就全国出名,下放新疆回来当上文化部长,才终获茅奖。你想想我的鲁院同学云南作家范稳连着两届:第七届第八届进入决赛,第九届才获得茅奖前十。我想想我的鲁院同学山西作家葛水平已经获得鲁奖等多种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这一次仅进入前百,排名远落无名作家陈元魁之后。
看来潘凯雄的眼光果然不错!看来我毛竹的眼光真还不错!写到这里我都笑了,你们笑了吗?
其实,我毛竹后来把第九届茅奖第一名获得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找来看,感觉比陈元魁的作品《花儿是心上的油》差,特别比陈元魁的《麒麟河》差得不是一点点。也就是说,陈元魁没有最终获茅奖,仅仅是因为陈元魁在全国无名气 无背景 无人气 无宣传。更有,陈元魁在青海作协无官职。人家参加茅奖的,王蒙曾是宣传部长,范稳与葛水平是省作协副主席。可是陈元魁不屑当官。陈元魁是作家中看破官场的真作家,这几十年痴心写作,远离官场人斗权争,却被青海人民追捧,却青海爱才的领导们挚爱。陈元魁的身份仅是一个退休老作家。连青海作协的兼职,陈元魁都不要。而陈元魁当兵进厂,写作半路出家,就连他的那些文凭都是带职学的,凑数的。而第九届茅奖以前,有作家评价:茅奖是各省作协主席间的竞争。更有人透露,这些年茅奖获奖者中唯一不是作协主席的也就是一个刘震云。可是人家刘震云在全国多出名?刘震云的作品在全国多轰动?刘震云的书销售中国不说,仅拍刘震云作品改编的电影国家就多次投入多少亿。
陈元魁与这些大家比,真是太弱了。陈元魁除了在青海小有名气,在全国根本名不见经传。陈元魁这个人与陈元魁的作品,在全国35个省市,无几人知道。也就是陈元魁参赛,其硬件只有两个,一个是推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赵萍编辑过硬,一个是其书作者陈元魁写作水平过硬。可以说,陈元魁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的一个”空手道“,没有任何”武器“,除去一切虚幻,用自己的写作水平与中国多少优秀小说家较量。
可是人家陈元魁的作品愣是进入了茅奖前三十七名。被陈元魁落下的包括贾平凹、高建群等等中国名家。陈元魁不简单吧?
以我毛竹的个人观点, 陈元魁的作品获茅奖当之无愧。当然,我毛竹还认为,最该得获茅奖的不是陈元魁的《花儿是心上的油》,这个有点儿镇不住;而是陈元魁的《麒麟河》(上下部)(也就是作家出版社副社长,如果当年没有把毛竹带到北京的《麒麟河》(上下部)退回青海,那么《麒麟河》最有可能获得第八届茅奖。也就是作家出版社退回青海的不是一部普通的作品,而一部本当获茅奖的作品。可惜呀!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惜。不知道作家出版的副社长想起此事会不会感叹)。
毛竹在这里,请中国有眼光的文友们找来书比较阅读,相信你们将得出和毛竹一样的结论。
也就是以潘凯雄的眼光,他看出的是一部获茅奖的作品,而不仅是一本仅获茅奖前37名的作品。
在这里毛竹再一次感谢潘凯雄导师对小毛竹点过去书稿的识别。
滚滚红尘书稿芸芸,全国无名的作家写的好书稿,多么需要有更多类似潘凯雄编辑家这样的大识别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是一种风雨大识别,这是一种雷电大识别。背景是现在出版界编辑跟多跟风,追星,追利。背景是现在纸媒一片“秋风秋雨落叶潇潇”。
陈元魁印象:
陈元魁,贾宝玉在青海投身转世
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
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我总也是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更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那时的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只有文学创作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创作可让我渡过冥河。
这个青海的贾宝玉,他的名子叫陈元魁。
陈元魁老师的头出奇的大,身子就显得小。
认识陈元魁老师是我到青海日报投稿。那时的我整日多愁善感,甚至有些悲世厌俗,更是有些无助绝望。可是他却对生活是那样的热爱。他说起他怎么在大冬天站在街头看几个孩子在路边的水泥桩子上做作业,一看就看几个小时。他对生活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
他说他怎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第一位妻子死去,心里是说不出的恐怖和凄凉。他带我去看他的第二位妻子: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却被他的爱滋润的如同一个灵鸟。陈元魁评价第二位妻子有这样一句话,这么多年我都记得:“一句话只需说一遍,她就永远记得,根本就不需要再说第二遍。”而一个农村妻子身上的安静真的让我感动。
而我一个城市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安静下来?为什么生命中总有那么多的骚动燥动律动激动震动颤动?我为什么整个如同一个片秋风中瑟瑟的红叶,被狂风吹着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不下来?
和陈元魁老师认识了那么多年,开始我这个小毛丫头并不是特别在乎他的。他把我当成知音,给我看他写的还没有发表的手稿,可是我并不认为写得有多么好。我甚至虚妄地以为,如果我写,我会比他写得还好。因为我总身不由己成为焦点人物,本就站在“爱的中央”。描写自身的感受,当然比那些站在外面的人容易得多,准确得多。
我只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心情不好时、自信心不够时、自卑感特强时、感觉自己绝望得要崩溃时,感觉自己驾驭不了自己生命这匹野马时、总想犯乱时,总想毁灭时,我便飞也似地跳到他身边去照镜子。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
而他对我的全方位的赞美,也是避免自己崩溃的外力。
而那个特定时期我实在也是愿意到一个能欣赏我、能赞美我、能鼓励我的大朋友那去。就如我那一段时间,本就是破的就是碎的,需要这种欣赏这种赞美这种识人这种知音让我试着重新粘合拼凑破碎的自已.我总也是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激情感受感觉迷惑迷茫迷惑。更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
那时的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的我是高傲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只有文学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让我渡过冥河。那时我讨厌那些跟在我屁股后面追我的男人。那时的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太丑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总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周围的人。世界真实向我展示其断面,与我童年少女时的相差太大,对我的冲击力足以致命。那时的我只要交一些“中性”的朋友。当然别人是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更有许许多多的议论漫天漫地的议论是跟随着我的。
小小的西宁真是太小了。
我到他那里照镜子还感觉在乱世中他能给我一种安全感。我到他那里照镜子还因为只有他能照见我的丰富的内心、照见我内在的感受、照见我心灵的泉水、照见我树上的飞鸟、找在我的深山的珍藏、寻到我多年的恪守、照见我精神世界的富贵、照见我自认为的“钻石价值”。因为在我眼里他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既欣赏我又珍视我既爱护我又敬畏我,既有危险又没威协。那是特定时期的我所需要的朋友。
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我总也是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更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那时的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只有文学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让我渡过冥河。
第一次重视陈元魁老师是那一次到茶卡盐厂采访---青冀两省散文笔会。陈元魁看起来十分的忧郁,总是跟在参观的队伍的最后面,如同一个小小的尾巴。而这个小尾巴总是有撼动人心的发现:工地全部停工了,只有一个小风车还在那里独自旋转,左三圈右四圈。每一次不知道为何都奇怪地多出一个半圈。我看过去果然是。那独自转动的小风车有一种陈元魁身上才有的灵动,才有的凄迷,才有的孤独,才有的自信,才有的笃定,才有的无助。我的心里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个队伍尾巴尖尖上的小人人,第一次让我看到了他是在人群中,还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笔会上大伙儿让陈元魁唱歌,他便唱了青海花儿直令。和陈元魁接触这么久,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好这么感人的声音。从那以后每当听到青海的花儿王:朱仲碌、马俊等唱青海花儿时,我都会认为是陈元魁在唱。真的太像了!
有一次我和妹妹小米拉去陈元魁老师家,看到他家中堂的墙上居然挂着青海著名书法家里果的字:《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作者甄士隐。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字是立排的如斜斜飘飞的细雨,斜斜飘飞的落叶,更有一种神秘大雾出没其中,当下就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心里充满了魂动魄动风动雨动雷动地动星动惊动震动:这诗怎么能放在中堂?特别是那句,这仿佛是放在墓碑或是遗址或是一面刚出土不久的斑驳残墙上才是的呢。
知道陈元魁老师喜欢《红楼梦》,知道他写作追求《红楼梦》的语言风格,知道他和贾宝玉一般多愁善感。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把这首诗挂在中堂。我常想:中国这么大,华人这么多,可是把这首诗放在中堂的墙上,可是能只有陈元魁一个人。
而红楼梦中有四首歌,每一首都特别好听,最好的是宝玉清唱的那首《红豆词》,真可谓荡气回肠:
红豆曲——《红楼梦》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楼
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
展不开的眉头
捱不明的更漏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而每当听到这歌,我就会想起堂屋挂着《好了歌》解把红楼梦悲凉气场引入自家厅室的陈元魁.
有一次回青海,妹妹小米拉对我说:“你写的书都是啥?我怎么就看不进去?也看不懂!你看人家陈元魁写的《麒麟河》我就能看懂,还能看得津津有味。”姐姐毛美睫也说陈元魁的书她从朋友那借来一本用了三天三夜一口气看完了它。而我知道我的破书我的姐姐也说看不懂没看完,被甩在一边。
我心里太惊奇了;我的书有一部分写毛家家史毛家故事的,我的姐妹都没有看完,可是她们却都看了陈元魁老师的书
有一次回西宁,陈老师请我吃火锅,我当时忘了我从内地到青海本来火就大怎么可能吃红汤子的火锅?而那天晚上陈老师带我去见青海的著名书画家王云等,我还见到我的大学老师、书法爱好者王学功。当时唱歌,我嗓子已经开痛仍用英语唱了《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有说:“士为知已死,女为知音‘歌’”。陈元魁给出的评价是:“特别震撼!”可是当晚我的嗓子如同冒火焰一般,发烧到近四十度,大病一场。我这才明白青藏高原的厉害,每次回去都要病一场。从此以后回去我便小心翼翼。但是一想到是为了给陈老师唱歌,心又想,那些年,绝望时遇知音,病一次又何妨?这不是说,人生间真的曾有过自己认可的知己?
我知道,几年不见,陈元魁老师在埋头写《麒麟河》,但并没有出书。我向陈元魁老师索要,他居然寄给我一推杂志。每个杂志上刊出的只有他的一篇。而这样的杂志据我所知,杂志社只能给他寄一本或两本。那是作者需要永远珍藏的。可是他却全给我寄来了。以后每每想起这事我都我深深感动。我细细看反复看,的确是写得好,带着《红楼梦》的大气场,还有流出《红楼梦》的大伤感,还有《红楼梦》的大悟性,还有《红楼梦》的大悲凉。我想这部作品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它因该是真正写西宁的好作品。
陈元魁老师是青海人西宁人,对青海文化的悟透,使得这本书成为珍惜的青海民间文本。 陈元魁的祖籍和其它西宁人不一样,不是南京的竹丝巷,而是陕西西安附近 ,陈元魁的骨底流淌着秦文化的大气场。
当年,陈元魁的父母没有儿子,想要一个儿子,可是多年不能如愿。有一次有人对陈母说西宁南山下的大成寺求子很准,陈母亲就去了,用红线系住了送子观音娘娘胳膊窝下的一个小娃娃。没想到回来真的就怀孕了,生下了陈元魁。陈元魁的父亲早死,母亲后来也离开了他,这使得陈元魁变得比一般的男人多愁善感。
于是我把这本书草稿背到了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可是却是久久没有动静。后来听说书稿退回去了。我心里又是淡淡的伤感。后来听说青海人民出版社可能出版。我才感到些许的慰藉。
最近听说陈元魁老师的《麒麟河》终于出版了。听文友说:陈元魁断了和他们的联系。不知道陈元魁是不是用全部的存款积蓄都用来出了书《麒麟河》,身无分文才不出来接待朋友了。我知道他是十分在乎朋友的,对朋友的每一次不经意的牵挂,每一次不经意的问候都铭记
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我总也是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更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那时的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只有文学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让我渡过冥河。在心。这样的人怎么会和文友们断交呢?我百思不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在我的记忆中陈元魁是十分好客的。
我出来闯世界十几年,在青海西宁家中呆的时间一共加起来才几个月,可是我居然三次在大街上碰到他。这种“萍水相蓬”使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份的。
有一年回青海,我爸爸在青海医院住院。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小女护士。小女护士听说我是一位记者,便问我认识不认识青海日报的陈元魁。小护士说这几句话时,脸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小酒涡。这两个小酒涡楚楚动人地旋转着,隐现着,颤动着,梦现着,神回着。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少女的美丽,涟漪般迷雾船在小护士脸上忽然出现。有一种绽放露水般亮丽在迷惘中出没着追捕着。啥叫少女怀春?啥叫春水荡漾?啥叫清泉涌动?啥叫娇羞袭人?啥叫草春二月?啥叫珠露盈盈?那一瞬我才算是真正领教了。那张少女的脸颊,真是要多生动有多生动,要多水灵有多水灵,要多神秘有多神秘,要多迷离有多迷离,要多美丽有多美丽。我不楚望痴了多去,很久很久。
我心想,这小护士,一定是自以为遇到了一位真正知道欣赏爱护珍惜少女美丽的男人才可能出露这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生动?
我心想,这小护士,一定是自以为遇到了一位真正知道女人是珍宝的男人才可能出现这般忽然敛聚出来的美丽。
我心想,这个陈元魁从滚滚欲流中浮出,代表着人类世界终于存在着像贾宝玉一般把女人当人看的男人。
我心想,这个陈无魁从茫茫人海中浮出,代表着现实世界终于存在着像贾宝玉一般能窥探女人内心的男人。
我心想,这个陈元魁从滚滚红尘中浮出,代表着这个世界上那种致命尊重女性珍惜女性爱护女性欣赏女性的贾宝玉还没有绝种。就如恐龙还没有真正绝种一般。
我心想,这个陈元魁从事俗文人中浮出,代表着编辑中真的有不把女作者当可食上钩鱼儿的真的存在。
有一天,我和陈老师谈他的《麒麟河》,我说:前半部分写得挺好,甚至超过了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前半部分,甚至可与贾平凹的《废都》前半部分相媲美,可是后半部分距离却拉开了。你知道中国有两个男人一个是贾平凹,一个田易新,这两个男人是中国所有男人中承认自己是弱者的男人。贾平凹写自己得了肝炎在铁栅栏后面眼巴巴地望健康人亮丽地生存,田易新的动漫人物小破孩被小丫揪来揪去,踢来踢去。这两个男人就是因为承认自己是弱者故而引来了中国大气场,获得了比任何一个逞强男人所没有博大气场。
我说:你也算量是一个勉强承认自己是个弱者的男人。可是你的弱已经把浩浩荡荡的中国大气场引来了,可是你骨子里却又挺自信的,不肯真正弱下来不肯真正躺下来接着世纪长风,不肯彻底放松让这岁月悲风从你的身体的河中流过。我们酸文人是最弱的人群,你已经承认了,可是你却还在里面拗着,梗着,拗着,不肯真正放松不肯躺平了接这个世纪大气场,让它长长的流过。我是想说,你的《麒麟河》前半部分写得实在是好,把悲凉的大气场引来了,可是后半部分却与那大气场拗着、咯着,故而后半部分特别是结尾写得不理想。
最近我给陈元魁打电话,我说:“陈老师,听说你的书《麒麟河》出来了。是我买一套还是您送我一套?”“那当然是我送您一套。”我又问他“听说你最近不理文友们了,是不是因为自费出书伤了你的心?”陈元魅说:“不是!原因很复杂。我的书也不是我自费出的,是青海投资出的,在青海就卖了三千本,本全回来了,我还挣了四万。”我听到他这么一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说“太好了!在青海那么小的地方居然可销三千套,真的不错了。如果全国推一下可能会更好!
几天几夜看完《麒麟河》,心里充满了憾动。这真是一本十分珍贵的青海民间历史,且是孤本。它的深邃和厚重再于它从东方灵个人的命运重现了青海近代史。有许多透出真实信息的细节是难忘的:主人翁东方灵的爸爸被饿死,妈妈晚年儿子不在跟前死前的怨怅,解放初文人生活的拮据,独子没能尽孝的悔恨,特别是那个执拗的铁匠耿三锤........都被他写得维妙维肖。还让我撼动的还是那里面充满的大悲凉大欢喜大梦幻大迷茫。
而陈元魁老师告诉我,他的六十多万的字的《麒麟河》(续集)六十多万字《民生集》也已经完成。我这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居然请他来北京推广也的书。知道他想见雷达,我这个封在像牙塔的小女子主动为他和雷老师联系。雷达我多年前就认识了,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对雷达老师说起陈元魁,我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憾动:这个陈元魁是一个多么执拗的写者,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声中,在滚滚红尘的风雷声中,有几个这样的执拗的写者。我忽然想起刚认识陈老师时,他正在写了一个中篇,让我看,我还有些不屑一顾呢,总觉得自己若写出个东西会比他写得好,虽然他是大编辑。到现在,有二十多年陈老师就这样一路写来,不论东西南北风。而陈元魁开始不会打电脑,他是用手写出百完字。后来学会了,又在电脑中打出《麒麟河》《民生街》《花儿怨》近二百万字。最近陈元魁另一本大作,再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赵萍。正在等待下文。
还有一个秘密,陈元魁为了写书,一只眼睛qgy已经看不清楚了。
而就是到现在我才明白,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间,上帝为什么把陈元魁送到了我的身边。虽然我只是自私地想去照镜子,虽然我无助地只想被他欣赏,虽然我绝望地潜意识里可能只想听他赞美,粘合破碎的自己,虽然我拗着犟着排斥着挣扎着不肯真正接受这个大朋友,执着地坚持地和他保持很远的距离,恪守宗教一般忍着世俗的误解恪守一种距离。
写到这里时,我禁不住再一次回望我的青海,我离开了多年的青海,感觉眼里有雾雨迷蒙。
这次回西宁,我和陈元魁老师又一次在咖啡厅激情长谈。他告诉我拿到《麒麟河》河的稿费后,他带着妻子去了一趟广东珠海。当我离青时,和他告别,他却又带妻子在十一长假到了青岛。
看来,这个“青海阿门了”和我一当年一样对大海情有独衷。而第一次看大海带给我这个“青海阿门”的撼动,可是能也只有陈元魁老师这个永远的“青海阿门了”可能复述。
近日,青海文友打来电话,说是陈元魁刚到他的办公室来推销自己的新作《民生街》,文友出于同情出于怜悯只好用自己的钱要了一百本,哄陈元魁说是办公室要。并说陈元魁还要写第三部曲。文友叹息着说:真是不明白,这是干啥吗?这是为了啥吗?
文友数落着,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心里寄予的又是包括自己包括陈元魁在的内的所有的真文人的怜惜。
对所有的生命的要求下不得不写的酸文人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致命地珍惜。
我想起同样悲壮推书的大诗人昌耀。
我说过,一般人推自己的书是落入俗套的,可是如昌耀、如陈元魁这样的大作家推自己的书那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凉而是一种悲壮。
怜香惜玉,而今天,我居然惜别的这个玉是一个大头男人,这个潜心字作十几年,只挣回几万稿费的大头男人,那是真正需要这个时代人们珍惜的“宝玉”。而我的心里又是那对大作家的怜惜,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
文友数落着,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诉伤感。
最近这个青海的贾宝玉又写完第三部长篇巨著《花儿怨》由我交给人民文学杂志社潘凯雄社长。春节期间,我在上海,潘凯雄社长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感谢我给他推荐了这么好的书稿。
不久陈元魁老师夫妻来京下塌我报。陈元魁这才告诉我,因为青海人民出版社已定出书《花儿怨》,陈元魁为了把《花儿怨》拿回来,由我毛竹交给潘凯雄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陈元魁还交了三千违约金呢。这,听得我的心里又是漫无边际的伤感。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看好《花儿怨》,且准备将来用《花儿怨》来冲击下一届鲁奖还是茅奖,可是毕竟《花儿怨》还没有出版,其中可能还会有许多的变数,但愿别因为我弄得陈老师两头空。特别是让陈元魁老师出三千违约金我毛竹心痛。
陈老师看出了我的顾虑。陈老师说:“不论怎么样,我无怨无悔。我写作这么多年。写作事业将是我的一生的事业了。这一次,只要能得到人民文学潘凯雄社长的认可,不出我也满足了。”
望着陈老师,我的心里又是漫无边际的伤感。
陈元魁与”秦文化“作家帮的神秘缘份
作者毛竹
青海无名作家陈元魁的小说《花儿是心上的油》在第九届茅奖评选中取得前三十七的好成绩。陈元魁这个无名作家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这里透露一个秘密,陈元魁虽然是西宁人,但是祖籍却是陕西西安附近。陈元魁家族在西宁也不过三代人。也就是说陈元魁可归入”秦文化“作家帮,
陈元魁取得的成绩,是”秦文化“作家帮实力的再一次显现。被无名作家陈元魁拉下的”秦文化“作家,有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苓等名家。
第九届茅奖参赛作家中,”泰文化“作家阵容强大。
除了陈元魁,有著名作家贾平凹同时有《老生》《古炉》两部作品入围,红柯则有三部作品入围。
在这份参评作品目录中,陕西省作协申报了贾平凹的《老生》、冯积岐的《粉碎》、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三部作品。除此之外,贾平凹的《古炉》由当代杂志社申报;高建群的《统万城》、王海的《城市门》、张浩文的《绝秦书》、王妹英的《山川记》由中国作家杂志社申报;红柯的《百鸟朝凤》由作家杂志社申报;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叶广芩的《状元媒》由十月杂志社申报;耿翔的《田韩堡》、杨广虎的《风云·党崇雅 明末清初三十年》由西安出版社申报;高鸿的《农民父亲》由文汇出版社申报;巴陇锋的《云横秦岭》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申报;田冲的《迷局》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申报;马奇昌的《铸剑为犁》由三秦出版社申报;陕西玉周的《新养老时代》由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申报;杨焕亭的《汉武大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申报。另外,陕西籍作家杜光辉的《大车帮》也由海南作协申报参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