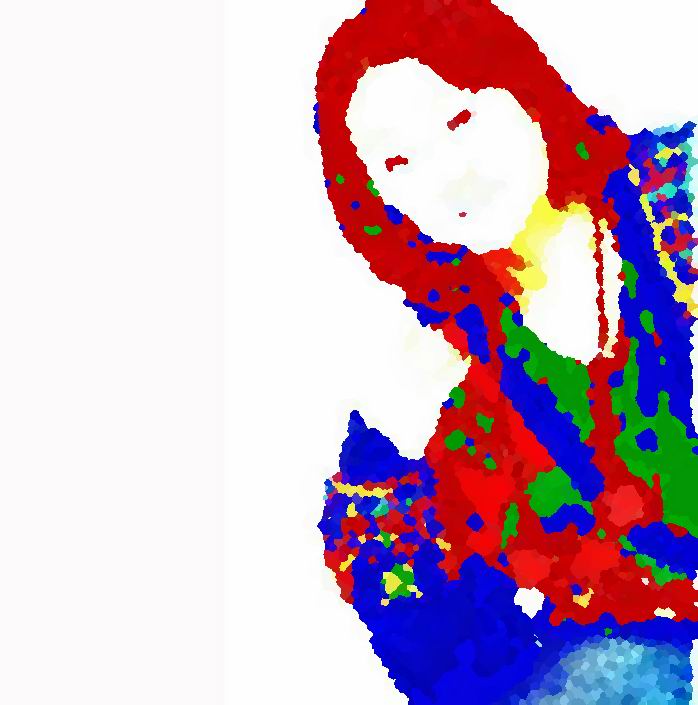
这个青海的贾宝玉,他的名子叫陈元魁。
陈元魁老师的头出奇的大身子就显得小。
陈元魁印象:贾宝玉在青海投身转世
大巴山野美女作家毛竹
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我总也是
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更没有想
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那时的我是自
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只有文
学创作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创作可让我渡过冥河。
这个青海的贾宝玉,他的名子叫陈元魁。
陈元魁老师的头出奇的大,身子就显得小。
认识陈元魁老师是我到青海日报投稿。那时的我整日多愁善感,
甚至有些悲世厌俗,更是有些无助绝望。可是他却对生活是那样的热爱。他说
起他怎么在大冬天站在街头看几个孩子在路边的水泥桩子上做作业,一看就看
几个小时。他对生活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
他说他怎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第一位妻子死去,心里是说不出
的恐怖和凄凉。他带我去看他的第二位妻子: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却被
他的爱滋润的如同一个灵鸟。陈元魁评价第二位妻子有这样一句话,这么多年
我都记得:“一句话只需说一遍,她就永远记得,根本就不需要再说第二遍。
”而一个农村妻子身上的安静真的让我感动。
而我一个城市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安静下来?为什么生命中总有那
么多的骚动燥动律动激动震动颤动?我为什么整个如同一个片秋风中瑟瑟的红叶
,被狂风吹着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不下来?
和陈元魁老师认识了那么多年,开始我这个小毛丫头并不是特别
在乎他的。他把我当成知音,给我看他写的还没有发表的手稿,可是我并不认
为写得有多么好。我甚至虚妄地以为,如果我写,我会比他写得还好。因为我
总身不由己成为焦点人物,本就站在“爱的中央”。描写自身的感受,当然比
那些站在外面的人容易得多,准确得多。
我只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心情不好时、自信心不够时、自卑
感特强时、感觉自己绝望得要崩溃时,感觉自己驾驭不了自己生命这匹野马时
、总想犯乱时,总想毁灭时,我便飞也似地跳到他身边去照镜子。而他脸如银
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
而他对我的全方位的赞美,也是避免自己崩溃的外力。
而那个特定时期我实在也是愿意到一个能欣赏我、能赞美我、能鼓励
我的大朋友那去。就如我那一段时间,本就是破的就是碎的,需要这种欣赏这种
赞美这种识人这种知音让我试着重新粘合拼凑破碎的自已.我总也是照完就跑,
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激情感受感觉迷惑迷茫
迷惑。更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
。
那时的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的我是高傲的。那时候我只
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只有文学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让
我渡过冥河。那时我讨厌那些跟在我屁股后面追我的男人。那时的我总觉得这
个世界太丑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总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周围的人
。世界真实向我展示其断面,与我童年少女时的相差太大,对我的冲击力足以
致命。那时的我只要交一些“中性”的朋友。当然别人是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
情。更有许许多多的议论漫天漫地的议论是跟随着我的。
小小的西宁真是太小了。
我到他那里照镜子还感觉在乱世中他能给我一种安全感。我到他
那里照镜子还因为只有他能照见我的丰富的内心、照见我内在的感受、照见我
心灵的泉水、照见我树上的飞鸟、找在我的深山的珍藏、寻到我多年的恪守、
照见我精神世界的富贵、照见我自认为的“钻石价值”。因为在我眼里他不是
男人,也不是女人。既欣赏我又珍视我既爱护我又敬畏我,既有危险又没威协
。那是特定时期的我所需要的朋友。
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我
总也是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更
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那时的
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
只有文学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让我渡过冥河。
第一次重视陈元魁老师是那一次到茶卡盐厂采访---青冀两省散文
笔会。陈元魁看起来十分的忧郁,总是跟在参观的队伍的最后面,如同一个小
小的尾巴。而这个小尾巴总是有撼动人心的发现:工地全部停工了,只有一个
小风车还在那里独自旋转,左三圈右四圈。每一次不知道为何都奇怪地多出一
个半圈。我看过去果然是。那独自转动的小风车有一种陈元魁身上才有的灵动
,才有的凄迷,才有的孤独,才有的自信,才有的笃定,才有的无助。我的心
里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个队伍尾巴尖尖上的小人人,第一次让我看到了
他是在人群中,还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笔会上大伙儿让陈元魁唱歌,他便唱了青海花儿直令。和陈元魁
接触这么久,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好这么感人的声音。从那以后每当听到青海的
花儿王:朱仲碌、马俊等唱青海花儿时,我都会认为是陈元魁在唱。真的太像
了!
有一次我和妹妹小米拉去陈元魁老师家,看到他家中堂的墙上居
然挂着青海著名书法家里果的字:《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作者甄士隐。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
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
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
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
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
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字是立排的如斜斜飘飞的细雨,斜斜飘飞的落叶,更有一种神秘
大雾出没其中,当下就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心里充满了魂动魄动风动雨动
雷动地动星动惊动震动:这诗怎么能放在中堂?特别是那句,这仿佛是放在墓
碑或是遗址或是一面刚出土不久的斑驳残墙上才是的呢。
知道陈元魁老师喜欢《红楼梦》,知道他写作追求《红楼梦》的语
言风格,知道他和贾宝玉一般多愁善感。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把这首诗挂在中堂
。我常想:中国这么大,华人这么多,可是把这首诗放在中堂的墙上,可是能
只有陈元魁一个人。
而红楼梦中有四首歌,每一首都特别好听,最好的是宝玉清唱的
那首《红豆词》,真可谓荡气回肠:
红豆曲——《红楼梦》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楼
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
展不开的眉头
捱不明的更漏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而每当听到这歌,我就会想起堂屋挂着《好了歌》解把红楼梦悲凉
气场引入自家厅室的陈元魁.
有一次回青海,妹妹小米拉对我说:“你写的书都是啥?我怎么
就看不进去?也看不懂!你看人家陈元魁写的《麒麟河》我就能看懂,还能看得
津津有味。”姐姐毛美睫也说陈元魁的书她从朋友那借来一本用了三天三夜一
口气看完了它。而我知道我的破书我的姐姐也说看不懂没看完,被甩在一边。
我心里太惊奇了;我的书有一部分写毛家家史毛家故事的,我的
姐妹都没有看完,可是她们却都看了陈元魁老师的书
有一次回西宁,陈老师请我吃火锅,我当时忘了我从内地到青海
本来火就大怎么可能吃红汤子的火锅?而那天晚上陈老师带我去见青海的著名
书画家王云等,我还见到我的大学老师、书法爱好者王学功。当时唱歌,我嗓
子已经开痛仍用英语唱了《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有说:“士为知已死,女为
知音‘歌’”。可是当晚我的嗓子如同冒火焰一般,发烧到近四十度,大病一
场。我这才明白青藏高原的厉害,每次回去都要病一场。从此以后回去我便小
心翼翼。但是一想到是为了给陈老师唱歌,心又想,那些年,绝望时遇知音,
病一次又何忍?
我知道,几年不见,陈元魁老师在埋头写《麒麟河》,但并没有
出书。我向陈元魁老师索要,他居然寄给我一推杂志。每个杂志上刊出的只有
他的一篇。而这样的杂志据我所知,杂志社只能给他寄一本或两本。那是作者
需要永远珍藏的。可是他却全给我寄来了。以后每每想起这事我都我深深感动
。我细细看反复看,的确是写得好,带着《红楼梦》的大气场,还有流出《红
楼梦》的大伤感,还有《红楼梦》的大悟性,还有《红楼梦》的大悲凉。我想
这部作品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它因该是真正写西宁的好作品。
陈元魁老师是青海人西宁人,对青海文化的悟透,使得这本书成
为珍惜的青海民间文本。
当年,陈元魁的父母没有儿子,想要一个儿子,可是多年不能如
愿。有一次有人对陈母说西宁南山下的大成寺求子很准,陈母亲就去了,用红
线系住了送子观音娘娘胳膊窝下的一个小娃娃。没想到回来真的就怀孕了,生
下了陈元魁。陈元魁的父亲早死,母亲后来也离开了他,这使得陈元魁变得比
一般的男人多愁善感。
于是我把这本书草稿背到了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可是却是久久没
有动静。后来听说书稿退回去了。我心里又是淡淡的伤感。后来听说青海人民
出版社可能出版。我才感到些许的慰藉。
最近听说陈元魁老师的《麒麟河》终于出版了。听文友说:陈元
魁断了和他们的联系。不知道陈元魁是不是用全部的存款积蓄都用来出了书《
麒麟河》,身无分文才不出来接待朋友了。我知道他是十分在乎朋友的,对朋
友的每一次不经意的牵挂,每一次不经意的问候都铭记
而他脸如银盘,男身女相,也真的像一个大镜子,适合我照。我
总也是照完就跑,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消化我那汩汩涌出的焦灼烦恼灵感。更
没有想过他也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男人。常常地居然忘了他的性别。那时的
我是自私的。那时的是自我的。那时候我只要事业,其它什么都不想要。似乎
只有文学可让我收拾覆水。似乎只有文学让我渡过冥河。在心。这样的人怎么
会和文友们断交呢?我百思不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在我的
记忆中陈元魁是十分好客的。
我出来闯世界十几年,在青海西宁家中呆的时间一共加起来才几
个月,可是我居然三次在大街上碰到他。这种“萍水相蓬”使我相信我们之间
是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份的。
有一年回青海,我爸爸在青海医院住院,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小
女护士。小女护士听说我是一位记者,便问我认识不认识青海日报的陈元魁。
小护士说这几句话时,脸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小酒涡,这两个小酒涡楚楚动人地
旋转着,隐现着,颤动着,梦现着,神回着。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少女的美丽
,涟漪般迷雾船在小护士脸上忽然隐现。有一种绽放露水般在迷惘中出没着。
啥叫少女怀春?啥叫春水荡漾?啥叫清泉涌动?啥叫娇羞袭人?啥叫草春二月
?啥叫珠露盈盈?那一瞬我才算是真正领教了。那张少女的脸颊,真是要多生
动有多生动,要多水灵有多水灵,要多神秘有多神秘,要多迷离有多迷离。我
不楚望痴了多去,很久很久。
我心想,这小护士,一定是自以为遇到了一位真正知道欣赏爱护
珍惜少女美丽的男人才可能出露这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生动?
我心想,这小护士,一定是自以为遇到了一位真正知道女人是珍
宝的男人才可能出现这般忽然敛聚出来的美丽。
我心想,这个陈元魁从滚滚欲流中浮出,代表着人类世界终于存
在着像贾宝玉一般把女人当人看的男人。
我心想,这个陈无魁从茫茫人海中浮出,代表着现实世界终于存
在着像贾宝玉一般能窥探女人内心的男人。
我心想,这个陈元魁从滚滚红尘中浮出,代表着这个世界上那种
致命尊重女性珍惜女性爱护女性欣赏女性的贾宝玉还没有绝种。就如恐龙还没
有真正绝种一般。
有一天,我和陈老师谈他的《麒麟河》,我说:前半部分写得挺
好,甚至超过了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前半部分,甚至可与贾平凹的《废都》
前半部分相媲美,可是后半部分距离却拉开了。你知道中国有两个男人一个是
贾平凹,一个田易新,这两个男人是中国所有男人中承认自己是弱者的男人。
贾平凹写自己得了肝炎在铁栅栏后面眼巴巴地望健康人亮丽地生存,田易新的
动漫人物小破孩被小丫揪来揪去,踢来踢去。这两个男人就是因为承认自己是
弱者故而引来了中国大气场,获得了比任何一个逞强男人所没有博大气场。
我说:你也算量是一个勉强承认自己是个弱者的男人。可是你的
弱已经把浩浩荡荡的中国大气场引来了,可是你骨子里却又挺自信的,不肯真
正弱下来接着世纪长风,不肯彻底放松让这岁月悲风从你的河中流过。我们酸
文人是最弱的人群,你已经是了,可是你却还在里面拗着,梗着,拗着,不肯
真正放松不肯躺倒接这个大气场。我是想说,你的《麒麟河》前半部分写得实
在是好,把悲凉的大气场引来了,可是后半部分却与那大气场拗着、咯着,故
而后半部分特别是结尾写得不理想。
最近我给陈元魁打电话,我说:“陈老师,听说你的书《麒麟河
》出来了。是我买一套还是您送我一套?”“那当然是我送您一套。”我又问
他“听说你最近不理文友们了,是不是因为自费出书伤了你的心?”陈元魅说
:“不是!原因很复杂。我的书也不是我自费出的,是青海投资出的,在青海
就卖了三千本,本全回来了,我还挣了四万。”我听到他这么一说,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我说“太好了!在青海那么小的地方居然可销三千套,真的不错
了。如果全国推一下可能会更好!
几天几夜看完《麒麟河》,心里充满了憾动。这真是一本十分珍
贵的青海民间历史,且是孤本。它的深邃和厚重再于它从东方灵个人的命运重
现了青海近代史。有许多透出真实信息的细节是难忘的:主人翁东方灵的爸爸
被饿死,妈妈晚年儿子不在跟前死前的怨怅,解放初文人生活的拮据,独子没
能尽孝的悔恨,特别是那个执拗的铁匠耿三锤........都被他写得维妙维肖。
还让我撼动的还是那里面充满的大悲凉大欢喜大梦幻大迷茫。
而陈元魁老师告诉我,他的六十多万的字的《麒麟河》(续集)六
十多万字《民生集》也已经完成。我这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居然请他来北京推
广也的书。知道他想见雷达,我这个封在像牙塔的小女子主动为他和雷老师联
系。雷达我多年前就认识了,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对雷达老师说起陈元魁
,我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憾动:这个陈元魁是一个多么执拗的写者,在经济高
速发展的车轮声中,在滚滚红尘的风雷声中,有几个这样的执拗的写者。我忽
然想起刚认识陈老师时,他正在写了一个中篇,让我看,我还有些不屑一顾呢
,总觉得自己若写出个东西会比他写得好,虽然他是大编辑。到现在,有二十
多年陈老师就这样一路写来,不论东西南北风。而陈元魁不会打电脑,他是用
手写出的《麒麟河》《民生街》一百二十多万字。
而就是到现在我才明白,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间,上帝为什么把
陈元魁送到了我的身边。虽然我只是自私地想去照镜子,虽然我无助地只想被
他欣赏,虽然我绝望地潜意识里可能只想听他赞美,粘合破碎的自己,虽然我拗
着犟着排斥着挣扎着不肯真正接受这个大朋友,执着地坚持地和他保持很远的
距离,恪守宗教一般忍着世俗的误解恪守一种距离。
写到这里时,我禁不住再一次回望我的青海,我离开了多年的青
海,感觉眼里有雾雨迷蒙。
这次回西宁,我和陈元魁老师又一次在咖啡厅激情长谈。他告诉
我拿到《麒麟河》河的稿费后,他带着妻子去了一趟广东珠海。当我离青时,
和他告别,他却又带妻子在十一长假到了青岛。
看来,这个“青海阿门了”和我一当年一样对大海情有独衷。而
第一次看大海带给我这个“青海阿门”的撼动,可是能也只有陈元魁老师这个
永远的“青海阿门了”可能复述。
近日,青海文友打来电话,说是陈元魁刚到他的办公室来推销自
己的新作《民生街》,文友出于同情用自己的钱要了一百本,哄说是办公室要
。并说陈元魁还要写第三部曲。
文友数落着,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感。心里寄予的又是
包括自己包括陈元魁在的内的所有的真文人的怜惜。
对所有的生命的要求下不得不写的酸文人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致
命地珍惜。
我想起同想悲壮推书的大诗人昌耀。
我说过,一般人推自己的书是落入俗套的,可是如昌耀如陈元魁
这样的大作家推书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凉。
怜香惜玉,而今天,我居然惜别的这个玉是一个大头男人,这个
潜心字作十几年,只挣回几万稿费的大头男人,那是真正需要这个时代人们珍
惜的“宝玉”。而我的心里又是那对大作家的怜惜,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的伤
感。
文友数落着,我的心里又是那漫无边际诉伤感。
最近这个青海的贾宝玉又写完第三部长篇巨著《花儿怨》由我交
给人民文学杂志社潘凯雄社长。春节期间,我在上海,潘凯雄社长亲自给我打
来了电话,感谢我给他推荐了这么好的书稿。
不久陈老师夫妻来京下塌我报。闻听因为青海人民出版社已定出此
书,陈还交了三千违约钱。听得我的心里又是漫无边际的伤感。虽然人民文学
出版上下看好,且准备用还没出的《花儿怨》来冲击下一届鲁奖还是茅奖,可
是毕竟《花儿怨》还没有出版,其中可能会有许多的变数,但愿别因为我弄得
陈老师两头空。
陈老师看出了我的顾虑。陈老师说:“不论怎么样,我无怨无悔。
我写作快一生了,这一次,只要能得到人民文学潘凯雄社长的认可,不出我也
满足了。
望着陈老师,我的心里又是漫无边际的伤感。

